李贺最恐怖的一首诗 第1篇
李贺有一种逆反传统的心理,在诗中他更愿意以一种不受拘束,灵活多变的结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综观他的诗歌,结构方式突出的特征是:起结无定,不蹈常规,章法跳跃,跌宕起伏。李贺诗呈现出奇特的艺术思维特征,结构呈现出一种拗折激荡之美。李贺心中的忧思和愤慨,是很难用一种平和舒缓的结构表现出来的。他的诗中意绪变化无端,时而低沉,时而亢奋,章句忽起忽结,有时甚至完全听凭直觉的引导,任由自己的想象超越时空自由流动。《梦天》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飒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前四句借助奇特的幻想,从尘世飞跃到天上,进入扑朔迷离的月宫,在广袤的空间里遨游;后四句又急转直下,由仙界折返尘世,关注人世的千古沧桑。诗句流转自如,忽起忽落,时空交叉错杂,意绪游移无端,想象飞腾,妙笔生花。再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前七句写仲春二月,花开草长,燕语呢喃,津头舞女长裙飘飞,末两句却转为凄厉之调:“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天上谣》前十句写天上之乐,末两句突然一声长叹,又回到地上:“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虚幻的乐被现实的悲一下子打得烟消云散。可以说,李贺所创造的奇特的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前所未有的。求生的意志、对天国的向往与人生的短促、现实的困厄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困扰着诗人的心灵,使他的精神常常处于亢奋与消沉交替起伏的状态,导致其想象变化倏忽,活跃异常。李贺的不少诗歌,特别是游仙诗都具有这种特点。李贺的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与意象源于他独特曲心理状态。
李贺诗的这种结构特点,可能是因为他太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客观事物的固有特征和理性逻辑被他刻意打乱了,让人觉得怪诞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贺最恐怖的一首诗 第2篇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李贺好言鬼事,因有“诗鬼”、“鬼仙”、“鬼才”之谓,但绝非专以“_”来标新立异、耸人视听。笔者认为,李贺对死亡世界的感受并不是单纯的恐惧,里面夹藏着诗人的融通感,甚至归属感。以《苏小小墓》为例: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诗歌在读者眼前铺展开一幅空灵飘渺而真切可感的图画:那个披风为裳、系水为佩的香魂,眼噙幽兰坠露一般晶莹的泪水,身乘碧草作毯、华松为盖的油壁车,徒然为无期的幽约燃起碧莹莹的灯烛,在西陵坟墓的凄风苦雨中竟夕相待。不仅苏小小的形象历历如绘,甚至连同她期会难成、情痴转空的哀愁都能被体会得到,这是由于李贺有意打通生死异路的遮隔,冲破了现实的有限时空,心灵才得以在幽明两界穿行往来,毫无滞碍地体会鬼魂的情愫。类似的情况还如:“左魂右魄啼瘦肌,酪瓶倒尽将羊炙”听到饿鬼们怨气冲天的哀嚎、“娇魂从回风,死处悬乡月”感知那客子死且不渝的乡情、“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体念武帝亡灵徒自悲伤的无奈……这些鬼物“彼虽异类,情亦犹人”i,但像的只是孤苦飘零、前路无望的人,因为死亡已将所有的意义抹去,死鬼们即便寸心不泯,也不过空余一缕幽怨。不难发现,鬼灵的特质实与李贺的心迹形成了同构对应的关系。极端地说,也只有鬼灵等死亡事象才能与李贺的精神状态达成同构。因为一般来讲,人活着总有翻身的希望,在自判永无出头之日的李贺看来,断难理解自己“一心愁谢如枯兰”的怨怅和绝望。由此,李贺与冥界的精灵们缔结了知交故旧一样相惜相伴的感情,这种感情在《秋来》一诗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李贺彻夜秉烛伏案,倾注毕生心力炼句苦吟,这些凝结着他浮生长恨的诗稿,却被时人轻弃,落得被花虫蠹蚀的下场。诗人一念至此,心下无比惨然惶惑,风雨涔淋中,但见先贤英灵前来存问,并邀他共赴秋夜莽原上的坟场,看那徘徊游荡的诗鬼,喁喁诵读着坎坝交车谋诗。坟土之下掩埋着千百贫士古今同恨的怨血,历经千年犹自不能消蚀。如果说《苏小小墓》是李贺对鬼魂情感的理解,那么这首《秋来》则写了鬼魂对李贺心迹的体谅,我们看到,当诗人�j惶无主之时,来施予安慰的朋友竟是些孤魂野鬼,诗人感到自己的境遇与那孤清凄苦的荒魂正同,故把安慰说成凭吊,将自己也化成孑然飘零的荒魂。杜甫《梦李白二首》有句云“魂来枫林青,魂反关塞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也说“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不知一个人在尘世中要如何孤独索漠,才会把这些虚渺的鬼灵引为知己,但我们至少可以寻绎这种体验的内在精神――超越欲求。不受知赏、不为世用的文士,在现实中饱尝世俗生活的苦果,于是把死亡世界当作可供期许幸福、寄托心曲的存在,在沟通人鬼、出入生死的神秘体验中实现超越跟解脱。
对死亡世界的神秘体验深深浸透了李贺的日常生活,以至寻常的景象也能见出鬼境,比如这首《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风白。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这本是一幅安谧明洁的秋夜田野图:皓月长空,和风万顷,池水清碧,虫声低细。却从四、五句开始变调,气氛转入凄迷诡魅:山间升起云雾,苔藓爬满岩石,冷风中的红花滴着露珠,宛如怯寒的娇娘滚落的妆泪。荒无人烟的田地里稻梗狼藉,有点点流萤在横斜的埂陇上空来回游曳。到收尾两句彻底将人间拉入鬼域:石缝里流出泉水,砸落在沙地上,明灭的磷火,如墓前的漆灯,点缀朵朵松花。
这是诗人体验的实景,还是他心造的幻境?笔者觉得很难区辨,但更倾向于前者,此诗应作于李贺辞官归乡后,骑驴背囊、竟日觅诗的日子里,笔触当跟从游踪飘至,而非凭空拈出,不过诗中造境,很显然是浮离于现实世界的。不论是野虫轻轻短吟,还是流萤幽幽低飞,都显得过分岑寂,不类人境,泉水滴落在沙地上,滞浊的闷响让人惊心,霜露中饮泣的红花,像极了烂漫醴艳的曼珠沙华,最后竟还点上一盏鬼灯,这哪里是人间田里,分明是黄泉路上。可见李贺每日出外觅诗,意图不在模山范水、描述见闻,他没有兴致描绘现实中的寻常景观,更不愿把感觉留在世俗人间,因为他在人间经受的尽是痛苦、囚束,唯有体验彼岸才能获得片刻的超脱、快乐和美感。
李贺最恐怖的一首诗 第3篇
李贺的鬼诗与仙道诗虽然都热衷于超现实意境的营造,但诗人的创作心态明显是不同的。李贺写鬼诗常常流露对死亡世界融通式的体验和对鬼魂知交式的理解深情,不过一旦涉笔仙道,便高扬起清醒深刻的生命思考。相比鬼诗中那种如梦似幻,恍惚难辩的迷离氛围,后者显得理智、冷静,充满质疑。李贺质疑那至美至乐的所在,底里是生命和价值深深的幻灭感,这噬人的死亡和附骨的苦难,纵使是飞仙幻想也不能解救,即便徜徉在怡神悦目的白云仙乡也不能遗忘,或许只有想到那幽冥世界里,与他共饮苦酒的鬼魂相伴时,诗人才曾真正收获一份此身不孤的解脱。那象征着死亡的世界,湿冷荒凄却在暗夜里流溢着魅惑诡谲的华光,这才是专属于李贺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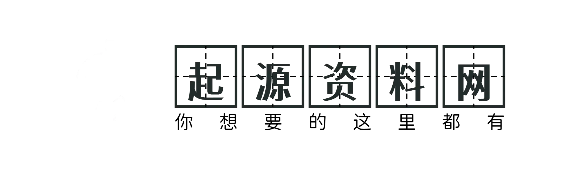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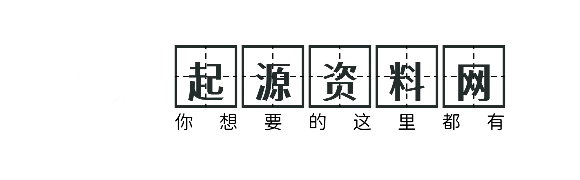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